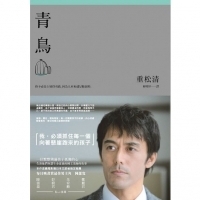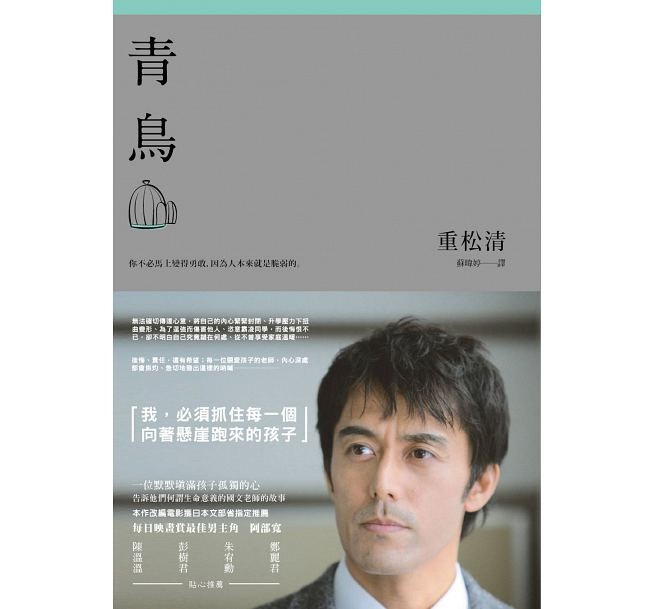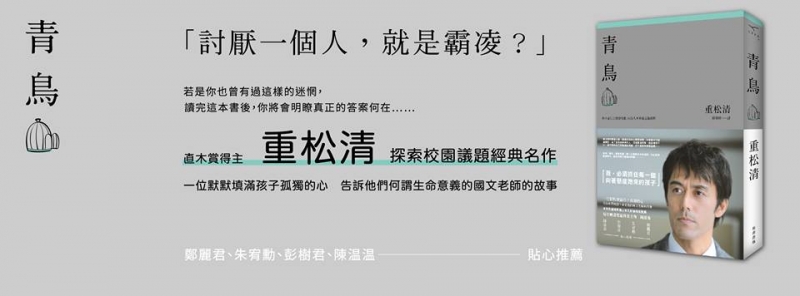
我們正在接受處罰。
有同學笑著說「不用在意啦」,也有人生氣地抱怨「這又沒什麼」。
「事情早就結束了,搞不懂那傢伙腦袋裡裝什麼啦!」
井上一面從二樓陽台向操場吐口水,一面振振有詞,不過其實那也是我們的心聲。
—沒錯,一切都已經結束了,真的都結束了。
每個人都深切反省了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們後悔莫及,也想向野口致歉;儘管也有井上這種搞不清楚有沒有認真反省的混蛋,但大部份男同學―以及我,絕對都發自內心、真誠懺悔了。
可是,光是這樣還不夠嗎?非得再多反省一點、更後悔一點才行嗎?
上課鈴聲響起,受處罰的一天又開始了。
老 師們從管理大樓的教職員室穿越走廊往教室前進,村內老師也在行列裡。井上發現了村內老師的身影,一面嘟囔著說「那傢伙超讓人不爽的啦!」一面走進教室。在 陽台的其他同學雖然不像井上那樣大剌剌說出口,不過八成也抱著同樣的心思;只見他們各自拖著意興闌珊的步伐,慢吞吞地回到教室。
我是最後進去的學生。二年一班的學生一共三十三人,教室裡卻排列著三十四個位子。在這些位子當中,有兩個是空著的;其中一個是我的位子,另一個則是野口的位子。我坐回自己的位子;靠窗那排從前面數來第三個座位處,野口的位子,一片空蕩蕩的。
站在講台上的村內老師,安靜地巡視教室,目光停留在野口的位子上;然後,他輕輕點了點頭,翻開點名簿。
「今天是十、十一月,狗、狗、狗……九號,星期四……對、對吧。」
村內老師說話總是結結巴巴的。明明是國文老師,卻連「Ka」行與「Ta」行,還有濁音開頭的字都講不清楚。有女生發出竊笑,也有男生低頭碎唸「真蠢」,井上則轉過身子,對周圍的朋友用氣音說道「爛透了」。
只要站上講台,即便想忽略,台下的狀況也一目了然,但村內老師卻毫不在意。他從容地確認今天的值日生,在點名簿上寫下「無人缺席」,然後抬頭看著野口的座位。
「早安,野口同學。」
村內老師微微一笑,用輕輕的聲音這樣說著。
今天的處罰開始了。
井上不斷用課本拍打桌子,焦躁地製造出巨大聲響。
老師沒有理會他,逕自向大家發起印有《學生會報》的紙張。
之前的班導高橋老師,總是習慣把一整排的資料塞給坐在第一列的學生,讓他們自己往後傳,不過村內老師卻會親自繞著教室,一張張發下去。他也發了一張給野口。老師拉開椅子,把紙張塞進抽屜裡。這大概也是對我們的懲罰吧。
他 來到我的座位,我將雙手夾在腿間,微微低頭。如果是高橋老師,肯定會大發雷霆,用凶神惡煞的表情警告我「雙手給我好好伸出來拿!」心情惡劣的時候還會用力 擰我的耳朵;但村內老師什麼也沒做,而且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默默地將《學生會報》放在桌上,然後一聲不吭地移往下個座位。
井上仍在用課本 拍打書桌,大概是因為被老師無視,所以鬧彆扭鬧得更兇了吧!「很吵耶,阿井。」―平常就與他不對盤的梅田低聲威脅道。井上嘖了一聲,像要把桌子砸爛般用力 拍了一下,然後把課本一把扔在桌上。教室裡瀰漫著一股尷尬的沉默,衝突一觸即發,煩躁與鬱悶在無聲中累積。
村內老師沒有對井上及梅田說話,繼續平心靜氣地分發會報;當他經過井上和梅田的座位時,也只是不發一語地將紙張放在桌上。
《學生會報》是十月開始編製的刊物,每星期一共發行兩次,在星期一及星期四發放。今天的《學生會報》是第十一號,A4大小的紙上寫著斗大的「東之丘中學‧新生活運動」。
上學放學的打招呼運動、午休的撿垃圾運動、設置義工委員會……
這些都是在星期二學生大會時決定的。然後,上頭還寫著,於學生大會時因時間不足而尚未表決的那項議題,「已經由總務委員會的三年級生與各位老師協議後獲得定案」。
「霸 凌輔導信箱的名稱定為『青鳥BOX』,源自童話故事《青鳥》的主題,『幸福其實就在自己身邊』。自本日十一月九日午休起,校內五個地點(教職員室前、圖書 館前、鞋櫃處、保健室前、體育館前)將設置信箱。遭到欺負的同學、目睹排擠的同學,不想參與霸凌、卻被團體逼迫的同學,請拿出勇氣,善用『青鳥BOX』。 信箱將於每週一放學後,由老師和總務委員會的學生打開確認。」
我是二年一班的總務委員。開會決定信箱名稱時,我也在場。
青鳥―這個名字是由三年級的某位學長提議的,我認為它一點也不好。說到底,若問我是否贊成設置霸凌輔導信箱,我一定反對。
但,我一句話也沒說。我沒有資格否決大家決定的事務。畢竟,不論是設置霸凌輔導信箱、發行《學生會報》,還是東之丘中學的「新生活運動」―讓校園重獲新生,一切都是我們二年一班所引起的。
發好刊物的村內老師,回到講台上巡視我們,說了句「早上的班會,到、到到到、到此結束」之後,便離開了教室。
「他真的很混耶,當什麼老師啊!」
井上故意提高音量,周圍的同學也紛紛點頭附和。
「阿井,你真的很吵耶!」梅田低聲吼道:「要抱怨不會去本人面前抱怨啊,白痴!」
「對嘛對嘛,孬種!」這次換成梅田身邊的人瞪著井上點頭幫腔。
教室的氣氛頓時凝重起來。
十月時,明明大家寫了那麼多悔過書,經歷那麼多次全班討論,彼此確認國中生涯最重要的就是友情與體諒,如今卻……
自從十一月村內老師來班上後、自從這名老師成為班導師後,同學們就變得情緒不穩、暴躁易怒。全都是村內老師的錯,因為他把原本收起來的野口桌椅,再次擺回了教室裡。
我一邊等待第一堂英文課的本間老師來教室,一邊看著野口的座位。
野口不在了。他再也―或許是永遠,不會出現在我們面前了;但是,野口的位子卻必須一直保留在教室裡。
明明不在,卻又存在;明明存在,卻又不在。
這就是此刻我們所受的懲罰。
---本文摘自《青鳥》一書,新雨出版
【本文出處。未經授權,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