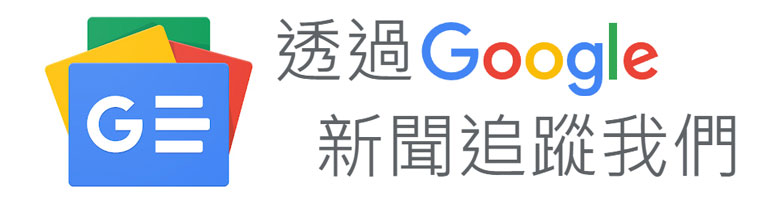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地區,與野生動物的共存問題日益顯著,其中最具爭議的便是野豬問題。野豬在香港既是自然生態的一部分,也因其滋擾性行為成為市區居民的頭號關注。近年來,隨著野豬數量的增長,牠們進入市區翻垃圾桶覓食、襲擊路人,甚至威脅公共安全的事件頻頻發生,迫使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控制牠們的數量。然而,對於野豬的處理政策卻在短短數年間經歷了戲劇性的轉變,從保護到絕育,再到大規模捕殺,這一切反映了香港在生態保育與公共安全之間的微妙平衡。本篇文章將探討香港野豬問題的歷史、現況和社會影響,並舉例說明牠們如何影響人類生活,以及政府在不同時期提出的應對方案。
近年來,香港的野豬問題愈發嚴重,牠們不僅在郊野地區活動,還經常闖入市區覓食,對公共安全和環境造成影響。野豬是一種雜食性動物,牠們以翻找垃圾為主要覓食手段,這導致市區多個地點的垃圾桶成為牠們的目標。根據政府統計,2024年香港的野豬滋擾黑點已減少至15個,但牠們的行為仍對居民生活構成干擾。例如,香港南區的深灣道便是野豬滋擾的典型案例,這裡毗鄰郊野公園且人流密集,野豬經常翻垃圾桶,導致垃圾散落一地,既污染環境又吸引更多野生動物,形成惡性循環。
除了翻垃圾桶,野豬還曾直接威脅人身安全。一些野豬因被餵食或接觸人類後失去了對人的戒心,甚至變得具有攻擊性。2021年11月,一名輔警在北角遭野豬咬傷左小腿,成為政府轉變政策的重要契機。同樣地,2024年打鼓嶺發生的野豬攻擊事件中,一名農夫在田間被野豬咬傷,漁護署隨後在當地展開捕捉行動,並「人道毀滅」相關野豬。這些事件揭示了野豬對市民的人身安全所構成的潛在威脅。2024年,漁護署針對農村地區的野豬滋擾問題進行了101次行動,共捕捉並「人道毀滅」224頭野豬。這進一步顯示野豬問題已不僅限於市區,而是對整個社會的多層面造成影響。
野豬在香港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數十年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香港城市擴張導致生境破壞,加上過度獵殺,野豬一度瀕臨絕跡。1960年,野豬甚至被形容為「極為罕有」。然而,隨著《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的實施,野豬得到了保護,數量開始逐漸恢復。到了1970年代,由於繁殖迅速,牠們的數量開始失控,特別是在新界農村地區,對農作物構成威脅。成年野豬每年可以懷孕兩次,每次生下4至6頭幼崽,使牠們的數量呈指數增長。
1981年,時任港督麥理浩應新界村民的要求成立了民間狩獵隊,專門處理野豬問題。狩獵隊由持槍隊員組成,每次行動均有警察監督。然而,2017年,漁護署接管了野豬管理工作,狩獵隊解散,並開始推行絕育和避孕計劃,希望能以較溫和的方式控制野豬數量。然而,政府認為絕育的速度無法追上繁殖速度,政策最終於2021年被終止。
此外,深灣道的野豬不僅翻垃圾,還曾襲擊途人。2022年,一名跑步愛好者在深灣道晨跑時,因驚動野豬而被追逐,雖無大礙但受驚不小。這些事件說明野豬的滋擾行為對市區居民的日常生活構成了不小的威脅,也進一步促使政府採取更嚴厲的管控措施。
最後,香港的野豬問題從歷史上的保護,到近年的絕育,再到如今的大規模捕殺,反映了城市化與野生動物共存的矛盾。筆者認為,雖然捕殺措施在短期內有效降低了野豬數量,但也引發了動物權益和生態保育的爭議。下篇將延續此話題,進一步討論香港如何在保育與城市化之間尋找平衡,並探討未來可能的解決方案。
更多中央廣播電臺新聞
台灣黑熊花蓮野放後續滋擾雞舍 受困陷阱獲救援
李嘉誠巴拿馬風波(二)隨時再來一次的修例危機
李嘉誠巴拿馬風波(一)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的最後一塊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