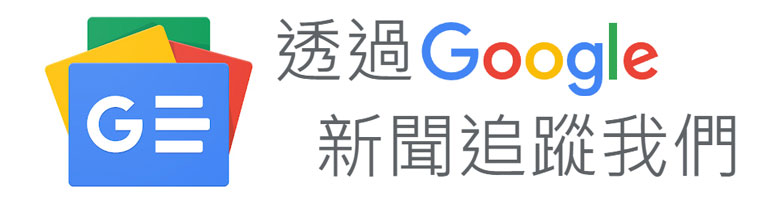有天坐捷運,見到一對夫妻帶著兩個小孩,一橫一直,橫的睡覺了,直的安坐位上。他間中會左右張望,但舉止非常安定。看到他的第一個反應是,難得有小孩坐下時居然不玩手機。第二是回想起我小時候,每逢坐地鐵都異常興奮。因為車廂就像樓下的公園,有吊環可用手抓緊半天吊,也有扶手柱子可以捉住旋轉。現在回想,不理解當時父母為何沒有阻止,或者他們已經習以為常,又或是我的情況已經超出控制範圍。
我覺得小孩生性都頑皮好動的,起碼我小時候遇到的朋友大多是這樣,但我特別嚴重,而且毫不聽話。無論學校還是在家,只要有人要求我做什麼、怎麼做,我偏向相反方向走。有一次到家附近的小學面試,媽媽非常希望我入讀此校,因為距離很近方便接送。據我媽憶述,面試期間本來老師說我成績優異,入學應該沒問題。最後我卻不知少了那條筋,在快結束時把桌上筆筒內的筆都翻出來把玩,面試結果可想而知。
類似的羞家(出醜)事件還有很多,例如突然在路上狂奔、在電梯內往死裡跳等。偶然父母會阻止,但多數都會讓我發瘋,等我累了、無趣了自然停下。因此我沒有什麼羞恥的感覺,很喜歡在課上講幹話回答問題,逗得同學哈哈大笑。老師有時似乎樂觀其成,畢竟問學生問題時,最怕空氣突然安靜。當然,老師和父母都有管教我守好基本禮儀,除非遇到危險情況,否則都甚少在我發瘋時對我喝罵或制止。
台灣管教孩子的方式似乎比較嚴格。雖然我沒有長期觀察台灣家長和老師是怎樣教育孩子,但從大學與同學相處中,可以感受到他們有種被壓抑住的感覺。例如在課堂上老師向大家提問,還是鼓勵學生提出問題,現場總是一片沉默,大家面面相覷。當初入學遇到這個狀況,我通常都會衝出來「大腳解圍 ( 足球術語 : 指比賽中球門受到威脅時,防守球員將球踢出危險區的意思 ) 」,舉手回應老師,好讓課堂繼續。
當時還是疫情期間,需要線上上課,同學們都未曾正式碰面。有天在宿舍走廊,一個陌生同學忽然跟我答話,原來是我的同班同學。他說因為我在課堂表現主動,所以特別印象深刻。在分組報告的時候,上台發表總是一個專責崗位。報告同學完全不用參與資料搜尋,或製作PPT的過程,只需要拿著其他同學的成品上台講。這個現象對我來說非常驚訝,在香港大家都會覺得要公平分工,所有工作大家都要參與,包括輪流上台發表。由此推測,台灣的教育甚少鼓勵學生提問,或是有某種規範,令學生不敢在課堂上發言。
在小學讀書時,曾經有班主任為了鼓勵同學們上課發問,推出提問獎勵計劃。每當同學在課堂上發問,就可以獲得一個印章,儲齊三十個就可以換取精美文具。班上隔天彷彿變成問答大賽現場,每堂總有半班舉手搶答或提問。但也有些副作用,有些同學會亂問問題胡鬧,例如突然舉手問老師時間,想說這樣也算有提問。
常有在台就學的香港朋友分享,覺得台灣的大學有點像中學,上課都是一言堂,學生都安靜的坐著。香港的大學環境充滿競爭,上課場地雖然大,但總有一堆學生坐在最前面,表現積極。當然不乏一些「戲子」,為了搏取教授給分數,裝作認真上課,暗地裡卻經常 Freeride。但總的而言,上課經常會有師生互動,課堂氛圍較開放自由,這可能也連接到香港的「執生」精神,就是重視變通的思考方式。
更多中央廣播電臺新聞
【香港雜記】深水埗排檔
【香港雜記】我的桌球時代
該如何檢視中國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