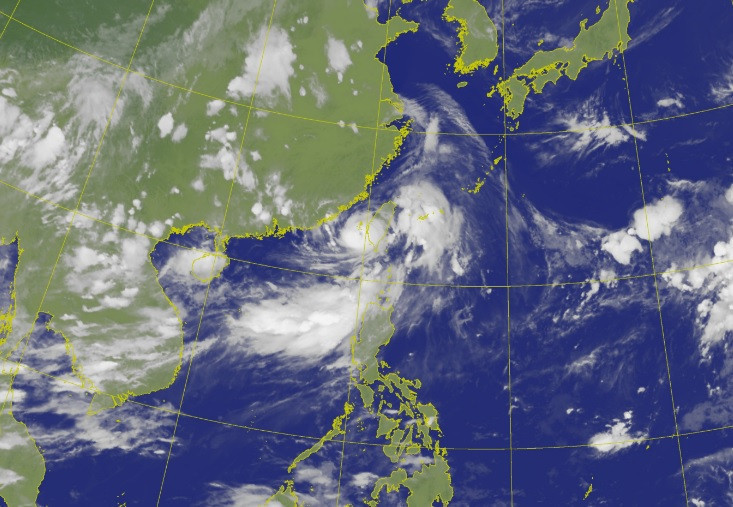小穗第一次來到我的診間時是夜診。綁著馬尾、一身運動服裝的她身材十分結實,帶著健康的小麥膚色。
那時她高二,課業成績優異,在游泳池畔的表現更是讓人驚豔。然而另一方面,從小學就開始顯現的妥瑞氏症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不間斷地困擾著她。
「小時候上課時,我只要一發出聲音,老師就叫我去教室外面罰站,甚至在放學後,把我留下來體罰。」
她雲淡風輕地描述著,我聞言不禁皺起眉頭。
「你不用擔心啦,現在的學校老師和同學都很好。欸,你這個醫師不錯,很關心病人,聽到我的過去還會皺一皺眉頭。你開的藥,我願意吃吃看!」
其實妥瑞氏症有藥物可以協助控制抽動症狀,但小穗過去從來不吃。我不知何德何能得到她的信任,開了妥瑞氏症和過動症的處方給她。對於新的藥物,她還算適應良好,妥瑞症狀稍有改善,注意力也進步許多。
高三的大學推甄,她上了教育科系。
「我這個暑假接了好幾場演講。」她興奮又帶點促狹地說:「很多單位想了解妥瑞氏症,你說有誰比我更適合讓他們『了解』呢?我簡直就是妥瑞氏live秀嘛!
回診時,小穗把一片光碟放在桌上。「這是我的演講,你有興趣可以聽聽看。」
講台上的她逐項解釋妥瑞氏症的症狀,說到發聲型抽搐時,突然「啊」了好大一聲,然後幽默地對台下的人說:「所謂發聲型抽搐,就像這樣。」聽眾都笑了。
演講的最後,她說:「我後來認為,妥瑞氏症對我來說是一個偽裝的禮物。我的意思是,這看起來是一件壞事,對吧?但它也讓我學到很多很多……你們學不到的事情。我相信這些在我成為老師的過程中,會讓我變得特別,跟別的老師不一樣。」
台下掌聲如雷,小穗如同一名精采表演後的演員,大方地彎腰向觀眾謝幕。

▲ 穢語症、抽動難控制!一位妥瑞氏症少女的告白: 「終於有個地方,讓我覺得自己是正常人。」。(圖:Shutterstock)
關上影片檔,我轉向眼前的小穗。她如同一個考試一百分的孩子般,期待地看著我,問我感想。
「你講得很棒,很精采,我想一定會為現場的妥瑞氏症孩子和家長們帶來勇氣。」
我讚許她,但同時仍不禁擔心這樣的曝光,其實也會對她造成壓力。我希望讓她知道,其實有時候可以不用一直堅強、樂觀沒關係。
「你說你接了好多場演講,最近還有游泳全國賽。我在想,你會不會太累?」我謹慎地說出心中的擔憂。
小穗聞言斂起笑容,情緒如同風雲變色,她突然間掉下淚來。「其實講了這麼多場之後,我越來越覺得空虛……」
她邊掉淚邊說著,在這樣的場合,她好像被當作一個「楷模」,必須樂觀、堅強,但是她其實也會失望、焦慮,也會對嘲笑、欺負她的人生氣。可是這些在演講中,她都不敢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聽眾所見的不是全部的你。」我說。
「那些負面情緒,我只能帶來這裡講。因為我怕聽眾知道的話,就會覺得其實我也沒那麼堅強、那麼好,就會不喜歡我。我已經被夠多人不喜歡了……」
一顆顆淚珠不停地從她眼中落下。
其實擁有喜怒哀樂,才是一個完整的人會有的情緒啊。沒有人每天心情都很正向、很樂觀。過於強裝的全然陽光其實不是真正的健康,而這也正是我對於小穗的擔心。
我說出這些想法,她靜靜地聽著。「這樣說一說,那種空虛的感覺好像好一點了。我想可能就是我的黑暗面一直在抗議吧,它們在說:『看我看我!為什麼都不讓我出來!』至少它們現在被看見了。」
小穗破涕為笑,又俏皮地演著。
上大學後,她依然每週坐火車回來看診。直到某次她眼角帶著傷來到診間,我才驚覺這例行回診對她來說是一趟多艱辛的旅程。
「你怎麼了?」我蹙著眉問,她的眼角腫了一大包。
原來她因為怕吵到其他乘客,搭火車時都站在車廂之間的連通道,根本沒進車廂。想到她一路沒有冷氣、顛簸搖晃地站著,我心中不禁一陣酸楚。
不僅如此,今天有個年輕男子在連通道抽菸,菸味的刺激讓她的穢語症一時控制不住,直接飆出類似國罵的聲音。對方看上去並非善類,直接揪住小穗的衣服,問她講什麼。小穗一緊張,穢語得更大聲,對方一氣就推她去撞車門。
「這根本就是傷害罪了欸!怎麼樣都不能動手啊!」我整個怒火攻心。
「這種事情,我們妥瑞氏症常遇到啦。每個都去告的話,我可能會變成律師事務所的VIP喔!」她竟然還有心情開玩笑。
接著她擔心地說:「欸,我跟你說這個,你不能不讓我回診喔。下次真的不會再跟路人起衝突了啦。我積了一個禮拜的心事要和你說欸!」
聰明如她確實猜中我的心思,我正想提出請她別再每週回診了。然而看著那渴求的眼神,我還是把這個要求嚥了回去,只請她下回務必要多加小心。
每週搭火車回診固然讓她有地方可以傾訴,但這一路上的危險和委屈,又豈是我所能想像?
雖然讀了教育相關科系,但令人驚訝的是,並非所有教授都理解她的症狀。友善教授的課,她自是出席率百分百,交出的報告被教授十分賞識,要她寫成研究計畫。不過碰到對她冷言冷語的教授嘛,她也不是省油的燈。
聽說某堂課的教授特愛叫她上課起來念課本,她一緊張,妥瑞氏的各種症狀樣樣來,最嚴重時甚至連穢語症都出來湊熱鬧。教授竟見獵心喜地抓住她的痛處,訓斥:「你對師長不敬,拿著課本去外面罰站。」
「去就去!教室外面藍天白雲,我幹麼待在那烏煙瘴氣的地方。我站在走廊越想越氣,就把課本撕下來,揉一揉從窗戶丟進去,可惜沒打到老師。」
毫不意外地,小穗的各科成績不是逼近滿分,就是被死當。眼見我又要開始碎念她的衝動行為,她急忙轉移話題。「我跟你說喔,上次帶我寫研究計畫的那個老師說,她可以幫我申請到美國交換。她說像我這樣特別的學生,美國那邊的環境比較開放,也可以去看看先進國家學校對特殊學生的服務。」
她的眼裡綻放光芒,彷彿已經呼吸到美國自由的空氣。
透過那位教授,她順利申請到美國交換生的身分,用參加游泳比賽存下的獎金與各種獎學金當旅費,開始興奮地準備要出國。
「到了那邊安定下來後,記得先去找學校的諮商中心,問問看有沒有人可以跟你定期討論你的狀況。還有,交換生的保險有沒有協助醫療這個部分……」
小穗臨行前,我還是很擔心她在那裡的醫療服務無以為繼,諄諄叮囑。
一年多後,小穗再次出現在候診名單上,依然一派運動穿著,背個大背包。
「嗨,好久不見。你很久沒出國了吧?給你看看金門大橋聞香一下。」
她掏出手機點開照片,快樂地說著冬天滑雪、夏天衝浪、各國的朋友、學校的泳池有多豪華……語速之快,倒像是怕我發問似的。
總算逮著一個空檔,問她回國後有什麼打算。
「我要回美國。」她勉強笑笑,又拿出手機,打開一張圖。「齁,我叫你看完這些照片,怎麼這麼沒耐心,你也ADHD是不是?來來來,你判讀一下這張影像。」
那是一張腦部核磁共振的影像,看得出有一顆不小的腫瘤。不是影像醫學專科的我,雖然看不出是什麼類型的腫瘤,但從不均勻的黑白顏色來看,也能知道那不是好東西。
「這是?……」我遲疑地問。
她雲淡風輕地笑笑。「有一天,我在游泳池邊正準備下水,突然間就不省人事了,後來腦部影像一照,就長這樣。」她不疾不徐地說著:「幸好不是在水裡,不然說不定我就溺斃,看不到你了,哈哈哈!」
「那,你回台灣治療了嗎?」我胸口有種悶悶的感受。
「那邊的醫師告訴我開刀的成功率極低,很有可能開下去就不會再醒來。美國醫師說的話應該很可信吧?所以我不打算治療了。」
她看起來仍然如此健康,完全不像身患絕症的人。我說不出話來。
「我這次回來,是想和我在台灣在乎的人們告別,也想告訴你們,我在美國過得很開心,我覺得那裡才是我的家。那裡的老師從來不會為了我發出聲音而責備我,朋友們跟我出去也從來不會覺得丟臉,甚至有路人不友善,他們也會保護我。你要我去找諮商中心,但我根本不需要,我在美國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正常人。你可以放心,我過得很快樂,我希望餘生在那裡度過……只是捨不得你們。」
我心裡不斷閃過要不要勸她至少去詢問神經外科醫師的治療建議,或是化療、放射治療的種種念頭。但我知道那只是出自我自私的盼望。
「所以,你已經訂好出國的日期了嗎?」到頭來,我只能問出這樣的問題。
「我希望越快越好。醫師說我的時間只有幾個禮拜了,只要那顆壓到腦幹,我隨時可能停止呼吸。我希望在那之前,可以回到我最快樂的地方。今天來,是想告訴你,我真的很謝謝你,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時刻,你這裡就是我的燈塔。」
結束看診時,我列印了回診單給她。
「幹麼還給我這個?」她看著手中的紙,笑著說。
「誰知道呢?說不定有颱風啊,班機會延誤啊。先幫你掛好,你不知道我的門診現在很難掛嗎?」我嘴上強撐地說著,心中卻已不是五味雜陳可以形容。
「好啦,你真三八。掰。」她瀟灑地站起身,對我一揮手。
一直到她離開診間,我都覺得彷彿下禮拜還會再見到她。
但我終究沒能再見到她。
幾週後,兒心醫師最忙碌的門診時段,突然有一個女生閃進門診。
「我是小穗的朋友。」她匆匆地自我介紹。「小穗她……這禮拜一走了……」
「什麼?怎麼走的?」震驚的我,連話都問不清楚了。
「應該是在睡夢中……她出國前交代如果她離開了,要把這些東西給你。」
她遞過一個牛皮紙袋,我放進抽屜。面對著長長候診的人龍,我深吸口氣,一個病人接一個病人地繼續看下去。
直到最後一位病人離開,外面已是深沉的夜晚。我獨自坐在診間,拿出牛皮紙袋。裡面是一疊厚厚的紙,還有一張卡片。
謝醫師:
當你看到這張卡片時,我應該已經不在了。說了再多次的謝謝也不夠,你千萬不要為我的離開而自責。幫我照顧好妥瑞氏症的小朋友們。
以後你看到白色蝴蝶時,記得那就是我。像出國的飛機一樣,對我來說,那是自由自在地飛翔。
小穗
我倒出那疊A4一半大小的紙,滿滿的回診單,一張一張都平整地保留著。從她高二第一次來看診,到前幾個禮拜,我最後一次硬塞給她的那張回診單。

本文摘自寶瓶文化《親愛的小孩,今天有沒有哭──兒少精神科醫師與他陪伴的風雨家庭》
【更多內容請上寶瓶文化粉絲專頁;本文由寶瓶文化提供,未經授權,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