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年十一月,中國的研究人員賀建奎(He Jiankui)聲稱,他編輯了人類的胚胎、也將其移植入子宮內,創造出一對名為露露(Lulu)和娜娜(Nana)的雙胞胎女孩。全球科學界立刻大力譴責他的行為。
他說他和感染了HIV病毒的爸爸們合作,透過抑制CCR五基因的方式,防止這些人的後代受到HIV病毒感染,因為,就是CCR五基因,會製造HIV病毒入侵細胞的受體。只不過,阻斷這個基因,也會提高其他病毒入侵細胞的風險。何況,醫師早就有能力,透過精蟲洗滌的方式,不讓帶有HIV病毒的父親,感染自己的孩子。
還有,基因編輯會因為所謂的脫靶效應(off-target effect)--也就是不小心移除了DNA上其他需要的部分--而有所風險。此外,基因可能有多重而未知的功能,以至於阻斷一個基因,可能導致其他預想不到的傷害。他沒有取得研究倫理委員會的同意,也沒有在動物身上進行初步研究,以證明這樣的基因編輯有用。他聲稱自己刪除掉的基因,可能根本不是他要刪除的基因。

(圖片來源:資料圖庫)
中國政府後來把他軟禁了起來。二○一九年三月,日內瓦(Geneva)舉行的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會議建議,頒布延後執行令,禁止將基因編輯完成的人類胚胎移植到子宮的研究,同時,要建置一套登錄資料,紀錄所有基因編輯的試驗。然而,二○一九年六月,一位俄羅斯科學家宣布,他計畫要在受到HIV病毒感染的女性所製造出來的胚胎中,編輯同樣的基因。
顯然,大家想問的是:這樣的延後執行令能延後多久、何時該終止這個延後執行令、由誰根據何種準則來決定是否延後還是終止,還有,萬一不是所有的國家或研究人員都遵守配合的話,該怎麼辦。
賀博士的行為,凸顯出這種基因編輯的應用,可能多麼容易,政府想完全規範或監管,都沒辦法。規範阻礙,在國與國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而且,這樣的阻礙,在中國和許多其他的國家,可能遠小得多。許多觀察家擔心,世界上的科學家,並非所有人都會遵守這個延後執行令。何況,病人和醫師經常都遊走在邊緣。舉例來說,二○一六年,墨西哥(Mexico)誕生了一個利用粒線體置換治療(mitochondrial replacement therapy, MRT)的寶寶。醫生從粒線體變異的母親身上取得卵子,移除其細胞核,再將其注入另一個細胞核也被移除的女性卵子內。接著他用父親的精子,讓這顆新造卵子受精,最後,製造出一個「三親嬰兒」(three-parent-baby)。雖然這對父母在麻州(Massachusetts)製造了最初的胚胎,而且負責的醫師來自紐約(New York),不過,由於美國禁止這個技術,所以,醫生和病人都到墨西哥完成這個手術。
一八八八年,英國的科學家法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引用表哥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著作,提出社會應該要鼓勵挑選「適者」基因的觀點。雖然「優生學」(eugenics)一詞在希臘文(Greek)裡的意思就是「好的基因」,但是,現在大多被定義為刻意挑選某些基因、揚棄其他基因的意思。許多觀察家擔心,現今病人根據一如身高、金髮藍眼、以及具備常春藤(Ivy League)學歷的特性,挑選捐卵者,這些選擇,便開始構優生學。
由於CRISPR技術快速發展,不久的將來,就有可能併入試管受精,這又會引起了其他的難題。史丹佛大學(Stanford)法學教授漢克‧葛利里(Hank Greely)就曾提出,未來,人類很快就會只把性交當成娛樂,而採取使用注射針筒和吸量管的試管受精法,選擇要不要給後代的基因,生殖繁衍。我們要有心理準備處理這些迅速的發展。
一份二○一七年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的報告認為,唯有在「沒有其他合理的替代方案」時,為了避免「嚴重的疾病或問題」,才該允許利用CRISPR技術製造人類的臨床試驗,不過,這樣的替代方案早就存在了--也就是透過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PGD),檢測胚胎。這項當前廣為運用的技術,以基因挑選出植入子宮的人體胚胎,其引起的倫理和社會關注,跟CRISPR技術引發的問題,極為相近。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提供了最接近我們當前需要從中學習的情況,它所所揭露的,就是我們需要做好準備處理的問題。
各國對於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以及其它輔助生殖技術)的處理方式,差異甚巨,因此,各國面對CRISPR技術的最終立場,也很可能有所不同。無疑地,基因編輯會繼續帶出風險,如脫靶效應、以及對後代的長期危害等等,因而陷我們於兩難,不確定這樣的手術,何時才「夠安全」,在未來運用這個技術時的兩個樞紐點上,這感覺會特別強烈--寶寶被創造出來,一開始是初步研究的一部分,後來則是牽涉層面更廣的臨床「轉出」的一部分。顯然,肯定要先建構足夠的動物實驗模型,然而,想要證實全然安全的話,也得追蹤第一個人類寶寶,直到他成年,同時追蹤他自己的孩子,評估其健康狀況。即使到那個時候,也還是有暗藏的可能危險,這在大部分經過核可的侵入性醫學手術上,都是會出現的狀況。
整體而言,CRISPR技術和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PGD)都會帶出潛藏其中的類似倫理張力,也就是醫師和其他人,要怎麼在各方面取得平衡--這些方面,包含了父母即使要對抗未來孩子身上可能的風險、還是有權利想要一個什麼樣的孩子;孩子有權利擁有一個開放的未來;還有,對於可能造成優生學同時威脅了社會正義的疑慮。現在,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會針對這些張力如何開展、怎麼處理的問題,提供非常重要的案例與獨到觀點。
大部分被視為符合社會期待的人類特性--例如聰明--看來都是社會與環境因素影響下、多種基因結合的結果。研究顯示,聰明有五○%是基因遺傳的,只不過,科學家尚未發現是何種基因。到目前為止,科學家檢驗了數百組DNA後,才發現一組最有智力指示性,而這一組也不過只能增加智力測驗(IQ test)分數一分而已。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許多基因的複合體,會與其他因素,彼此交互作用。
重要的是,吉姆和其他的生殖內分泌與不孕症專科醫生,現在就已經在面臨修改你我後代DNA的問題了:要改多少、該怎麼改。
話說回來,大部分的人,對於生育力、不孕症、或是這些用以改變我們後代子孫基因的新科技,都所知鮮少。大多數大學生年紀的男女,都高估了女性生殖力下降的時間點,也高估了一次性交後懷上孩子的機會,同時,還高估了試管受精的成功率。許多異性戀伴侶幾乎都不對外揭露他們曾經使用他人卵子、精子、或是胚胎的事情,也不提他們有基因變異、或者他們正想辦法移除後代的變異基因。這些話題,都帶有禁忌。
跟試管受精和「訂製高級寶寶」相關的醜聞和其他新聞,時不時就會出現在電視、雜誌、還有報紙的頭條,這些消息,還附帶了影像,或引人厭惡、或隱射奇蹟與提供希望,往往都聳人聽聞,過分「炒作」。二○○九年一月,領社會救助金過活的納迪亞‧狄尼絲‧鄧得蘇里曼(Nadya Denise Doud-Suleman)透過試管受精,生下了八胞胎,引爆大家一連串的憤怒與驚嘆。媒體很快地為她冠上「八胞胎的媽」(Octomom)這個名號,她的醫生麥可‧坎拉瓦(Dr‧ Michael Kamrava),則被稱為「八胞胎醫師」(Octodoc)。
二○一五年,媒體以頭條新聞的方式,報導了蘇菲亞‧維加拉(Sophia Vergara)的前未婚夫,為了爭取他們共同創造的胚胎的監護權,提告這位當時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女演員。他主張這些胚胎應該歸他所有,因此,即使維加拉小姐提出反對,但他有權將這些胚胎植入另一名女性體內,生養孩子。法院可不這麼認為。
科幻小說和電影也都探討過這些領域,描述這些技術在未來可能遭到濫用。《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就講述了一個用人造子宮製造人類的未來世界。在《巴西來的男孩》(The Boys from Brazil)裡,躲在巴西的前納粹份子,謀劃著要製造培育出一支亞利安(Aryan)複製人軍隊。電影《千鈞一髮》(Gattaca)描述的未來世界,人類一出生,就依據他們的基因,被嚴格分類到該屬的社會階級當中。在《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裡,一個極權主義式的神權政體,強迫有生育力的女人,要替「道德適配」(morally fit)的母親生育。諾貝爾獎(Nobel Prize)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作品《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描繪了一個未來的機構,他們製造並養育複製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這些複製人把器官捐給其他人。
話說回來,如今,每天都有人在使用挑選與製造人類的技術,讓無數的醫師與病人,面對著重大的兩難。想當爸媽,但自己不能生育、或是可能會把基因變異遺傳給後代的人,天人交戰地思考要不要利用這些機械式的干預。人類的選擇當中,沒有一種比起挑選基因、創造出我們這個物種的全新後代與成員的這個選擇,還要影響深遠。我們正直接打造著我們自己的基因革命,這是前所未有的。
「打造寶寶」可能會讓人聯想到科幻小說的情景:修改基因,創造出身高近一米九、金髮藍眼又聰明的超級運動員;不過,醫生和病人早就在利用新的技術,影響未來世代的基因組成,迫使你我面對這棘手的困境--身為自然所創造出的物種,人類對自己和其他物種,有什麼樣的責任。就象徵意義和基因而言,大人們透過孩子,延續自己到未來,這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只不過,比起過去,現在的做法,更有技術性,也更商業化。
因此,關於如何利用這些技術,我們現在面對的,是重要的道德、社會、文化、心理、還有存在主義的難題;是否要監督或控制這些技術,如果要的話,該怎麼監督控制;而更廣泛地說,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未來的方向為何、該不該朝那個方向去;還有,在這些領域當中,如果我們有責任需要擔負的話,那些責任又是什麼。
想要回答這些問題、曉得如何因應,我們就一定要了解,這些技術現在的使用方式為何、哪些技術受到採用、怎麼採用、誰採用這些技術、採用這些技術的時機為何、花費多少、由誰做這些決定、以及怎麼決定。
醫學文獻雖然提出了一些調查結果,不過,卻沒有回答許多關鍵的問題。儘管不少文獻有文章檢視以下這些議題--目前尋求過不孕治療的病人為數多少、年齡為何、成功率多高、還有他們如何處理牽涉其中的壓力--不過,這些資料並沒有完整地探討這些輔助生殖技術的多重運用和逐漸成型中的複雜世界。之前的這些研究,許多都是量化研究,並非質性研究,也因此,不一定有傳達出這些想當爸媽的病人,他們真切實際的經歷。
因此,許多的問題,還是圍繞在當今想成為爸媽的人和醫療提供者們,如何看待這些挑戰、及其背後更深遠的意義,然後做出決定。更大的議題,也隨著出現。新的科學發展,往往是一開始的承諾耀眼奪目,但不久後帶來的,除了好處以外,也有可能的危險。核融合帶給我們便宜的核能,也帶來了核彈。電子郵件和網際網路(Internet)雖然讓溝通更立即、更無遠弗界,不過,隨之而來的還有身分盜用與駭客的問題。從當前這些輔助生殖科技做何使用,所引起的重大問題,我們就可能看到自己的未來。
於是我決定要探索這個新興且快速演化的領域。我的指導教授之一,人類學家克里佛‧吉爾茲(Clifford Geertz)主張,我們要理解任何社會狀況,就應該先想辦法針對牽涉其中的個體們,取得其生活與大小決定的「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試著理解他們自己用自己的話所描述的觀點,而不是把外部先入為主的想法或理論架構硬套在他們身上。這樣的研究方法,不僅可以闡述這些個體所作為何,同時也能說明他們認為自己的所作為何、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行為以及面對的挑戰。
於是,我以訪談與問卷調查的方式,訪問了數百家不孕症治療提供者與病人--想像他們如何因應這些困頓--以勾勒出這個新領域的全貌。我普查了數百名醫生的知識、態度、以及行為,還檢視了數百個從事胚胎篩選與人類卵子買賣的複製生殖技術網站。
然而,讓人大感意外的是,沒有一本書曾經全面完整地探討過這些議題。因此,我決定寫這本書,把我所了解到的,呈現出來。
為了以最完整的方式揭露這塊新大陸,在本書裡,我會引用病人與臨床人員(醫師、心理治療師、還有護士)的故事,同時將這些群體與他們面臨的整體情況,描繪出來。總體而言,一如附錄B裡較為完整的資料所示,本書的焦點,放在我深入訪談過的三七個人的經歷上--其中有十七位醫師,十位其他不孕症治療提供者,還有十位病人。
這些醫生裡,其中一位自己也是不孕症病人,其他不孕症治療提供者,也有三 位是這樣的情況。我將這些訪談資料,做了系統性的分析,檢驗其中出現的主題為何。這本書同時也援引了多年來我跟數十位其他生殖醫師、醫療提供者、還有病人之間,大量的非正式對話內容,探討他們的經歷以及面臨的挑戰,以盡可能地通盤理解這些議題,進一步強化我對這些領域的了解。
這些臨床人員和病人,都透露了他們的希望、夢想、碰到的阻礙、顧慮、還有恐懼--那些「讓我夜晚輾轉難眠的事」。他們一致承認,自己涉及到的,是一個激進、新穎、而且近化快速的企業,製造出本來不會存在的孩子,在一個不尋常且前所未有的未知領域,謹慎摸索,小心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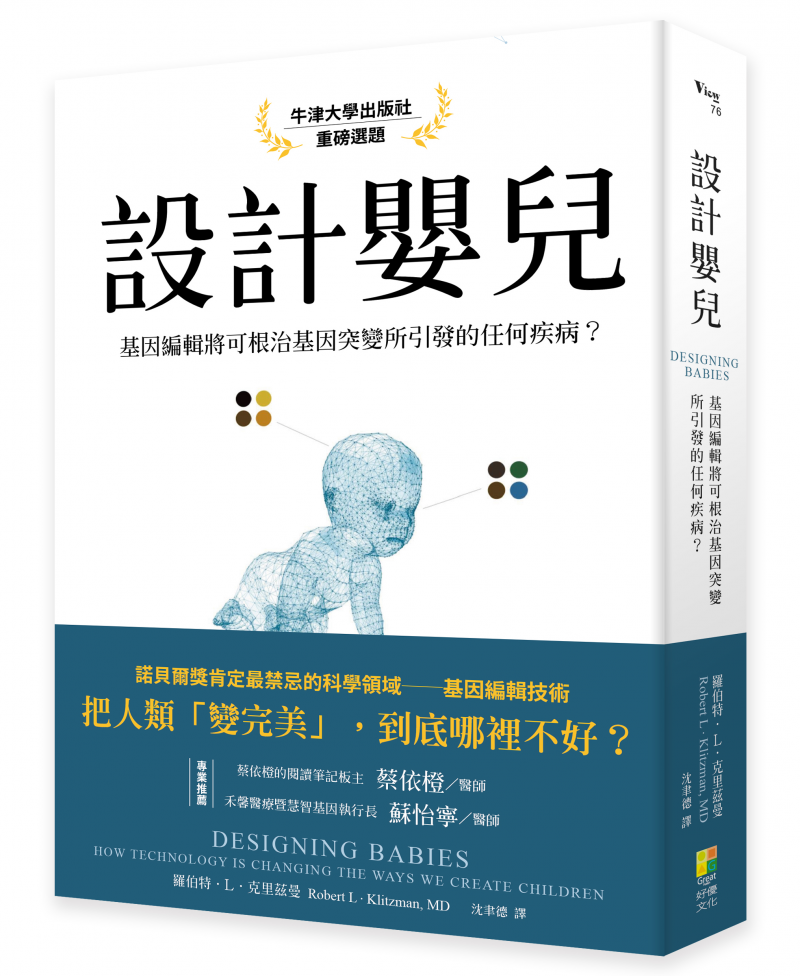
本文出自 出色文化《設計嬰兒:基因編輯將可根治基因突變所引發的任何疾病?》
【更多資訊請上《出色文化》粉絲團;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